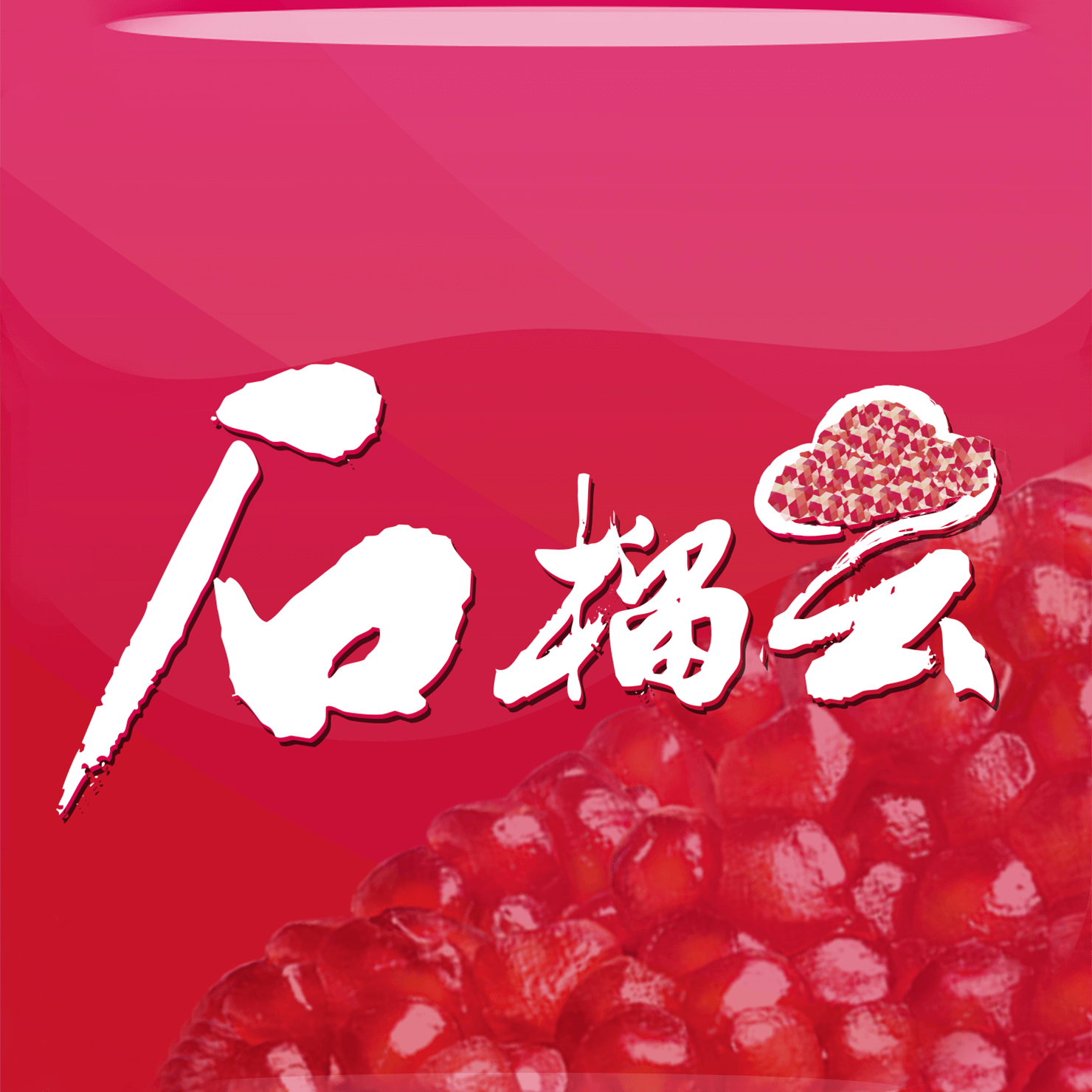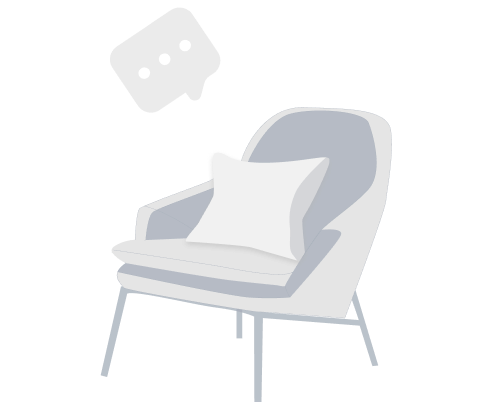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文化如涓涓细流,源源不断进入西域地区,西域学子们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下成长,共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李思敏/文
新疆文化既体现多元,更体现一体,这一体就是中华文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文化如涓涓细流,源源不断进入西域地区。西域地区各族百姓在学习和传承当地知识与文化的同时,也被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所吸引。

库尔勒市梨香小学师生在学校操场打太极拳。图/库尔勒市梨香小学提供
早在汉代,来自中原地区的儒家经典就已浸润着西域大地,出土于洛浦县的正面汉文、背面佉卢文的汉佉二体钱充分说明当时在西域地区汉文的广泛应用。《汉书》曾有关于龟兹王绛宾学习中原礼仪制度的记载,这表明当时西域地区的上层社会对中原文化的热爱。1993年,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汉简《仓颉篇》,与中原地区通用的启蒙识字课本《仓颉篇》一致,说明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学生已经开始使用与中原一致的识字教材。此外,在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出土的《论语·公冶长》,以及海头古城遗址发现的《战国策》残卷,都是汉代中原儒家经典在西域地区传播的实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国的经史典籍写本残卷,如《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学典籍。这些典籍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吐鲁番地区各族学生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实况。
隋唐时期,西域流行的语言文字种类丰富,包括汉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语言文字。吐鲁番出土《唐龙朔二、三年(662—66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中,多件文书涉及燕然都护府致安西都护府、西州都督府的牒文,均是用汉文写成;在哈密市出土的唐代焉耆文残卷《弥勒会见记》剧本,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长的一部焉耆文的文献;和田地区发现大量唐代于阗文的文献,其中包括少量世俗文书,奏报、信札、医书和词汇集等。唐朝在西域重要城市建立了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官学,为西域各族学子提供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唐代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抄本中不仅包含了《论语》的《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还附有六言《十二月三台词》、五言绝句六首和《千字文》数句。说明唐朝时期吐鲁番地区与中原一样设有私塾,并且与中原地区学习同样的经典,书写同样的汉字,这一时期西域地区同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不断增强。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契丹文、汉文、回鹘文在西域地区广泛的学习与使用。西辽统治者把契丹文、汉文作为官方语言文字推广学习。而在吐鲁番一带出土的当时的雕版印制品中,既有回鹘文典籍,也有大量汉文典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回鹘佛教僧侣学习汉语且水平极佳。同时这也说明虽然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政权更迭,时局动荡,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从未停滞,儒学始终发挥着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契丹民族尊崇儒学,西辽政权创立者耶律大石就曾参加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在西域立国后,西辽典章制度效仿中原,汉文成为官方文字,进一步体现了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原文化的滋养下,也出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该书中有大量“仁爱”等关于国家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阐述,这些思想与儒家文化同宗同源,说明西域地区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
元明时期,国家再次大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伴随着兴盛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多民族持续聚居交往,西域成为多种语言文字交融交汇的重要场所。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汉文、回鹘文、蒙古文、古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等语言文字,学子们充分学习各类语言,还出现一批以安藏等人为代表的翻译人才。多语并重推动了各民族文化频繁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勃兴和社会进步。同时,伴随着元明以来多元一体格局的持续深化,西域学子学习中原文化的形式更为多样。在这一时期,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东迁并定居在中原,他们尊崇儒学,学习汉文化,涌现了一批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翻译家、艺术家和农学家。如廉希宪,因其喜好儒家经典,手不释卷,被忽必烈称作是“廉孟子”。同时,西域地区的学校也继续将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教材之一,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1986年在且末县苏伯斯坎遗址出土的《西厢记》元代抄本残页,就是当时西域地区流传中原文学作品的实物史证,这侧面说明当时西域地区的文人学士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充分了解中原文化并具备鉴赏中原文学作品的水平和能力。
清朝时期,中国进入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新阶段。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原则,作为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新疆,很多民族传统文化被当地各族学子学习、传承,得以很好保留。清政府在新疆实行满语文、汉语文、维吾尔语文通用的政策,其中汉语、维吾尔语是各民族主要的交际语言,哈萨克语在北疆地区的使用也很普遍。不少民族的语言中出现了汉语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汉语蒙古语等语言合璧的现象,这加速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阿古柏入侵新疆后,使新疆的多元教育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清收复新疆后,为重建教育体系,并解决因语言不通导致的诸多问题,清政府广置义塾,聘请老师对当地学生进行授课,这些义塾不仅教授各族儿童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还引入来自中原的儒家经典,通过学习,当地各族学生对中原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同时,清政府鼓励新疆地区的孩子们参加科举考试,也培养出了一批通晓汉语和儒学的地方官吏,这些官吏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域学子们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更促使中华文化多元荟萃、百花齐放。这不仅体现了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更彰显了西域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源自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它将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今日和未来的新疆文化事业中,我们也应该不断汲取历史智慧,持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疆的浸润,不断增强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坚实纽带,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燕慧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